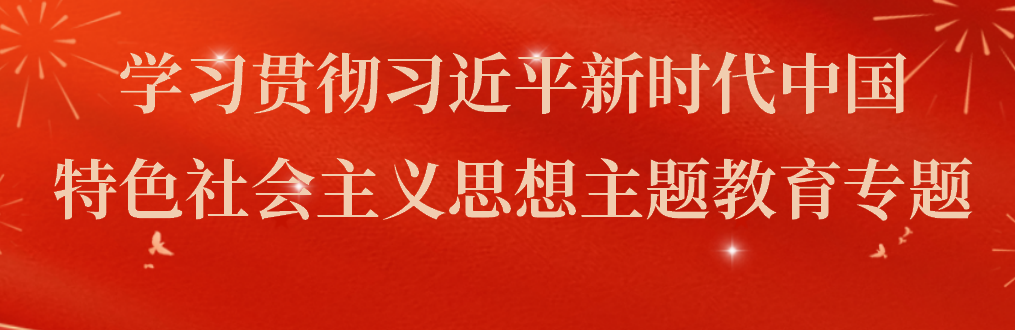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林斤澜小说论(1978—1982)
黄子平
……也还有少数真正的艺术家,飞翔在高天之下,波涛之上,只守着真情实感,只用自己的嗓音歌唱。波涛狂暴时,那样的声音当然淹没了。间隙时,随波逐流的去远了,那声音却老是清亮,叫人暗暗警觉出来,欢腾的欢腾的生命力。
——《林斤澜小说选·前记》
在当代作家中,再没有一个比林斤澜更让评论界既困惑又着迷的了。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的小说就以独特的成熟的风格,引起过人们褒贬不一的争论。中断写作十二年之后,近年来他写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说,一篇一篇的有味儿,一篇一篇的让人捉摸不透。把他“前后分作两截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可真是两截呀,有着明显的变化”。这一批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的作品(在与他同年龄的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思想的深邃和独到,艺术探索的多样和奇特,这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在评论界小心翼翼的沉默中取得的。打破沉默的评论家(往往是最有见地的),对他的作品却读得不细,论述是印象式的,学术性不强。林斤澜寂寞地,以惊人的耐心开辟着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也以同样惊人的耐心寄希望于未来。“时间,将助他一臂之力!”“待若干年后人们冷静地回过头来,重新评价这段文学史时,林斤澜的小说将会受到重视。”是的,相信时间的公正的人,都具有双重的信心——对于社会审美水平的发展,对于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用林斤澜自己的话说:“这好,这豁亮。这有浪漫主义气息。”
然而林斤澜是为现时代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贴近着现实生活,而且熔铸了与同时代人相通的真情实感。说到底,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不完全是由作家本人的主观体验决定的,仍然是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产物。对于真正的作家,新形式只能是新的生活内容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的艺术独特性是不容漠视的。如果同时代人不能阐明这一独特性,那就不仅表明,某种理解生活的角度、方式被忽略,同时也说明,进入作家独特的艺术视野的这一部分现实,却是我们的盲点。时间会给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以应有的报偿,时间却不会原谅买椟还珠、错失良机的人,他们不善于及时地珍视寂寞的探索者的劳动,把成败得失的点滴经验吸收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
他能等待,我们能么?
真情实感中提炼出来的魂儿
林斤澜是一个极其尊重艺术规律,不倦探讨艺术规律的作家。在一次讨论青年作家的小说的座谈会上,他说:“艺术的内部规律中要有一个魂儿,这个魂是什么呢?我请教过很多老前辈,有一次我请教一位教授,他讲了一句话,叫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内部规律中的魂,真情实感是从你的社会生活里来的,也是从你的政治生活里感受到的,它又是内部规律联系外部规律的东西。……一切的结构,一切的语言,我们都是为了表现由真情实感提炼出来的魂。光有真情实感,没有提炼,就会焦点模糊。焦点两个字,我是从托尔斯泰那里搬来的。他说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应当有一个焦点。又说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射出去。又说这个焦点不可以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它们完整的内容只能由艺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
这段话很关键。对于我们理解林斤澜的创作实践,有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必须通过细心捉摸作家的每一篇小说,从总体上有机地把握他的全部作品,去找到他从真情实感中提炼出来的“魂”,那个最重要的焦点。其次,我们又不可满足于这个抽象出来的“魂”,还要按照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考察这个“魂”是怎样渗透到他的选材、结构、人物、情节和语言中去的。同时,我们又不可过于生硬地坚执这个抽象的“魂”,去肢解作品的艺术整体,使它的丰富性具体性化为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
这里涉及了近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文学创作中的“主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在于我们多多少少都把艺术创造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了。反映本质就得把偶然性冲洗得一干二净,为了主题鲜明就让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它的对应符号,反对概念化就提倡无主题,强调形象思维就排除理性。“主题先行”还是“生活先行”竟也成了问题,仿佛创作过程可以从作家的生活实践中毫不粘连地剥离出来,仿佛主题的酝酿和成熟不是贯串于生活和创作的无尽环节之中。“主题”这个术语被我们弄得如此枯燥,如此僵硬,因此林斤澜用“魂儿”这个词,就亲切,水灵,有生气,是有血有肉的整体里跳动着、喧嚷着的东西了。
林斤澜把这个“魂”又叫作小说的“内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内里面’,就分出了高低”。而这个“内里面”,是从生活的“内里面”来的,是扎在生活里,含辛茹苦,蒸酒酿蜜得来的,绝不能“凭空而来”“传染而来”“偷盗而来”“耳提面命而来”。他强调了“魂”所必备的两个特点:它应是作家自己的、独特的;它应是从生活中来的。
真情实感怎样提炼出一个魂儿呢?林斤澜举契诃夫为例:“契诃夫对当时小市民的生活有很多真情实感,他把它提炼到一块时就是庸俗。有人说他的小说主题都是反庸俗,反庸俗就是他小说的‘魂’。”我们必须把他提到的这个例子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高尔基在谈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讲过:“在俄国,每个作家都真是独树一帜,可是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他们团结起来——那就是去认识、体会和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因此,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最可宝贵的主题是在于提出了“怎么办?”以及“谁之罪?”这一类重大的问题。作家的总主题总是在一时代民族的总主题制约下展开的,这一点具有普遍意义。我认为“五四”以来六十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它的总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每一个作家自己的总主题都是在这一时代的总主题制约下展开的。人们对我们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认识都在深化。对于“文化大革命”后从事写作的作家,无论他写的是什么题材,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都必然影响他的全部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将由于这一体验的深刻与否,独到与否,而分出高低。
林斤澜近年小说中,有一半是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生活的。其余作品,或者历史跨度更大一些,写到了战争年代,或者只写这几年的现实生活,也无不与作家对过去的思考熔铸在一起。他说:“我算算日子,整整十二年没有写作了。重理旧业,不光是生疏,还觉得堵塞。仿佛有些沉重的东西,搬也搬不走,烧化也烧化不掉。”我觉得,这些“沉重的东西”,正是使作家的艺术风格发生极大变异的原因。重要的是,他从这些沉重的东西里,提炼出什么样的“魂儿”呢?
在本节开头所引的那次谈话里,林斤澜讲道:“有位前辈作家说,……感受很多,要写好,得先提炼出一个意念(和这里说的魂差不多吧),他提炼的结果是一个字——‘变’,有人把感受提炼为‘疯狂’。”我们不妨大胆揣测,他所说的“有人”,就是林斤澜本人。
有作品为证。题为《神经病》《邪魔》这样的小说不用说了。
《卷柏》写了一个精神病顽症病人。《肋巴条》里老队长的老伴在那年月里气疯了。《阳台》《一字师》的主人公都有着不合时宜的怪癖。《腾身》里的老太太动辄发神经。《记录》的结尾是这么两句:“建议:送精神病院检查。医生提问:谁是病号呀?”林斤澜围绕着这么个独到的“魂儿”,写了一系列的小说。真好像他笔下那个《肋巴条》里的老队长,当人们问起他的老伴的病怎么得的,他冷静地、简简单单地答道:“感冒。”
……感冒两个字,是他沙里淘金般淘出来,又经过千锤百炼,这是精华,他再不给多添一点废物,也不给减掉一点光彩。只是变着法儿,对付不同的惊讶疑问,一会儿是一叠连声:
“感冒感冒感冒……”
或是拉长语尾:
“感冒——”
也有一字一顿的时候:
“感,冒。”
“疯狂”主题在林斤澜笔下,以冷峻、严厉、深沉、尖刻、嘲讽、诡奇的笔调,得到了反复多样、丰富具体的变奏,写出那个颠三倒四的年代里,可悲可怕可笑的疯狂气息,塑造出一批“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林斤澜不写悲欢离合,哀婉感伤,却专注于发掘表面冻结了的心灵深处,生命与人性的尊严,自由与责任的分量。他不写血淋淋的专横残暴,阴险毒辣,却勾勒带疯狂气息的思想、理论和举动,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特征。
这是思考的文学,有着与当代文学相通的思考和理性的特征。由于这个深刻独到的“魂”,使他的思考具有独树一帜的光彩。他不像刘心武那样夹叙夹议,呼唤着给被污染的灵魂金色的“立体交叉桥”;他也不像王蒙那样,裹着大量的回忆、俏皮话和新鲜感受的生活之流,咏唱失而复得的新中国的青春。他的思考完全渗透到艺术形式里去了,产生了一系列艺术变形的特点:奇特夸张的人物形象,突兀跌宕的情节,客观、冷静、非严格写实的手法,浓缩到了不能再浓缩的结构,简洁冷隽的白描语言,甚至某些细节的不真实和非逻辑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把那些沉重的东西,“搬也搬不走,烧化也烧化不掉”的东西,搁到读者心里去。让同时代人都来咀嚼民族的苦果,思索时代的总主题。
正是在这一点上,林斤澜的小说接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源头之一——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崛起的高峰,他的光辉照耀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我们读高晓声时想到《阿Q正传》,读张洁时想到《伤逝》,读湖南作家群时想起了《故乡》《风波》,读王蒙时想起了鲁迅的杂文。鲁迅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多种源头,无论主题的延续,人物典型的积累,艺术样式的丰富,风格的熏陶,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永不衰竭的生命之泉。而《狂人日记》,则是对古老中国发出的第一声彻底的不妥协的抗议,那“忧愤深广”的声音透过六十年烟云仍响在我们耳边。鲁迅一气儿写了三个各具特色的神经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白光》里的陈士成。他对这一特殊性质的艺术形象的关注,不能仅仅用先生精深的病理学知识和对俄罗斯文学(果戈理、安德烈耶夫)的爱好来解释。这更应是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独到深邃的理解和洞察的产物。“狂人”主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延续演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需指出如下一点也就够了:如果说,鲁迅经过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深刻体验了中国封建主义的顽强性,那么,当代人,更体验到了这一顽强性的可怕!这一体验从内容形式两方面都得到了深化。因此,林斤澜的小说不仅师承了先生忧愤深广的思想主题,而且从艺术上延续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
人物形象往往是作家思想艺术的结晶。林斤澜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着几分奇特。不是像铁铸一般冷静而沉默,就是飘飘摆摆,眼睛闪着怪异的微笑。倘若我们以为从“疯狂”主题出发,作家写的必然都是狂人,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林斤澜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很清醒的正常人(《卷柏》除外,这一篇在后边还要谈及)。林斤澜在这里仿佛只用了最简单的艺术手法:人物和环境的强烈对比,就达到了一种震撼性的艺术效果。
细琢磨,就不那么简单。人和环境的不协调,可以是人不正常,也可以是环境不正常。一般的心理,认为环境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不能适应环境是自个儿出了错。用《阳台》里的话说,是“不合身份,不合时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不少读者觉得林斤澜的人物不太真实,原因就在这里。有一位老师说:“看见学生的大字报错字连篇,自然很痛心,但那时绝不会去改它的。”这也不无道理。这就用得着作家提炼的那个“魂”了,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匠心所在。在某些年月里,作家经历苦难,却有一种禀性,一样品格,一种信念像真金火烧不化,永难磨灭,不屈不挠。那必定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固执,与生命熔铸在一起的东西,林斤澜把它提炼出来,作为人物性格中的主导特征,加以夸张、廓大、渲染,以致成为一种怪癖,一种无意识的举动,一种永恒不变的品性。这就是林斤澜小说人物中最具“林斤澜特色”的东西。
但是这样写要冒双重风险。首先,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很可能破坏其中之一的真实感。倘人物是真实的,环境就像插在人物背后的风景画片。倘环境是真实的,人物就像皮影戏。显然,过去的经历记忆犹新,作家略略几笔就能勾出真实的环境气氛,于是人物的真实性就很可怀疑了。其次,夸大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写实小说的大忌。有一个现成的贬词叫作“类型化”。这种人物表现一种单一的思想或品质,在小说里从头到尾其性格是不发展的,一出场我们就认得他们,合上书他们也跑不掉。
正是在这里,表现了作家“一意孤行”的艺术胆识。
首先,林斤澜坚持他的人物是正常人,这从他对“神经病”这一称呼所采取的嘲讽口吻就可以知道。我们也同意,并且争辩说:“如果……”作家会打断我们说,在他看来,正常的就是真实的。在不正常里活出来的正常,比我们通常理解的真实还要真实,是深一层的真实。
其次,林斤澜正是要写出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里始终不变的品格,突出那一点貌似平常却是民族性格里永难磨灭的可贵之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笔下的人物甚至连外貌也几十年没有丝毫的改变。《一字师》里,语文老师吴白亭,几十年都是那么个小老头,胖胖的白里透红的指头,点到错字上,落下星星点点的粉笔灰。《肋巴条》里的老队长,“他脸上一道道皱纹,横的竖的能连成圈儿,一圈一圈好像那叫作‘螺丝转儿’的烧饼,多少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仿佛十五岁上就这样,现在五十了也还这样,他没少也没老”。这些人物使我们想起大地上的山峰,铁铸一般沉默、坚定,多少风雨过去了,还是耸立着,“天欲堕,赖以柱其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农民,中国默默无闻的脊梁。
再次,由于正常的人物与不正常的环境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对比,使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呈现某种复杂性,显示了“正常中的不正常”和“不正常中的正常”。像《阳台》里的“红点子”教授,“他不但眼神,连身上都有一种奇异的光彩,……断不定是疯狂的邪光,还是创造发明的光芒。这两样好像是有不容易区别的时候,试看弹钢琴的,弹到手舞足蹈的霎时间……”,“要说红点子的神经是正常的,怎么连几岁的小学生都不如?有专政队里发展党员的吗?要说他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他怎么不胡说别的呢?”这就使得人物性格多了一层因素,微微隆起,向立体化过渡了。
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照着“文学概论”写作。他们往往“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自铸伟辞。我们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完全忽视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艺术特性,把主要是根据长篇小说创作实践归纳出来的艺术准则,变成一种“学究式的尺度”,来硬套在短篇小说上。短篇小说可以完全不描写环境。人物必须鲜明有力,一出场就抓住读者,却不一定要展开他的性格。即使是长篇小说里,有许多“类型化”的人物,如狄更斯的匹克威克,《三国演义》里的莽张飞,也一直活在世代相传的人们脑海里。这种经过夸张、渲染的性格,能包含的内容比一般批评家所想象的要丰富,其生命力也不比那些离开了他的环境、出身和成长的全部细节就说不清的复杂性格弱。林斤澜笔下的人物,鲜明有力,易记,但又大都具有冷静、寡言、深沉、内向、坚韧的特征。这种性格不那么表面化,不那么单一。作家又用自己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感情力量使他们“抖动”起来,使你并不发觉他们的“单薄”。但是,这种经过夸张的、不发展的性格,必须是喜剧性人物才是最成功的。如果是正剧或悲剧性人物,每次上场都高喊“我要复仇”或“我痛苦死了”,读者就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字师》里的吴白亭比《阳台》里的红点子更令人可亲可信的缘故。
这里论及的只是与林斤澜的那个“魂儿”有最直接关系的那些人物形象,远远不能概括他的小说人物的全部丰富性。为了把握线索,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许许多多线索以外的东西,但是在叙述时只能专注于与线索有关的部分。以上我们论述了作家独到深邃的“魂”渗透到人物形象时产生的特点,这就接触到了林斤澜最重要的艺术手法——艺术变形的规律。
“我自己的东西不完全那么写实”
人物性格的夸张是一种艺术变形,它的生命在于真实。既是客观真实的廓大,同时也是主观真实(真情实感)的灌注。从根本上说,等同于生活真实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艺术(广义地说)就是变形。用文字来固定“流动着的现实”就是一种变形。用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来“舀取”广阔的生活之流就是一种变形。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狭义的、与“写实”相对而言的艺术变形:包括夸张、扭曲、抽象、幻化、写意等等艺术技巧和手法,可以在中国古典画论和戏曲表现中找到它们的美学渊源。如果我们不认为文学只是现实的抄袭,就应该重视艺术变形的规律。因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创造的主观能动性,作家的思想感情力量和主观倾向,无不与这一规律有关。而自觉地运用艺术变形规律的作家,更能达到现实生活内在的真实。
林斤澜的《头像》(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篇很值得重视的小说。他写了一个默默无闻的雕塑家梅大厦,住在大杂院里,像个老泥瓦匠,生活上还是个老光棍,身衰体弱,却有一双“皮肤紧绷,肌肉鼓胀,伸缩灵活的年轻的手”。这双年轻的手在寂寞中固执地追求着艺术的创造。“在着力民族传统之后,追求了现代表现之后,探索着一个新的境界。”林斤澜精心描绘了梅大厦创作的一个木雕头像:
这是一块黄杨树顶,上尖下圆,留着原树皮,只上尖下圆地开出一张脸来。原树皮就像头发,也可以说是头巾从额上分两边披散下来。这脸是少妇型的长脸……那比例是不写实的。头发或者头巾下边露出来的尖尖脑门,占全脸的三分之一,弯弯的眉毛,从眉毛到下边的眼睛,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我的天,这么长这么长的眼皮呀。眼睛是半闭的。这以下是写实的端正的鼻子,写实的紧闭的嘴唇。这是一个沉思的面容。没有这样的脑门和这样长长的眼皮,仿佛思索盘旋不开。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伞盖一般笼罩下来,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这个少妇头像,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这个头像如果不能概括林斤澜自己全部作品的艺术特征,也相当凝练地表达了他所刻意追求的艺术境界。作品的“内里面”的东西,生活的底蕴,作家的匠心独运,不在写实的鼻子和写实的嘴唇那儿,而在那长长的眼皮,那半闭的眼睛,在那长长的眼皮的后面。你不由得相信,这沉思的眼皮一抬起来,就会“好像打个电闪,真伪好丑立刻分明……”而所有那些非写实的部分,都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上。如果说纯熟精到的写实部分构成了有生活实感的基本层次,那么非写实的部分就突出了作品的思想层次或哲学层次。
小小说《卷柏》篇幅最短,结构也相当单纯,最能说明上述特点。写的是一个顽症精神病人,含冤坐了十年牢的厨师。在医院里,经常蹲在墙根里,屈膝贴胸,下颏搁在膝盖上,双手放在脚面上,一言不发。这一症状的描写具有病理学意义上的严格真实。这是所谓“胎儿姿态”,是一种对外界一切都持警惕的自我保护姿态,是精神病里的危症。作家却从这里生发出一个寓意,一个象征:“我是卷柏。”卷柏是厨师家乡山岩上的一种蕨类植物,在大旱之年曲蜷着灰蓬蓬的叶子,待到有了水分,便又舒枝展叶,活过来了。人变卷柏,卷柏变人。这里与卡夫卡《变形记》里小资产阶级卑微恐惧的心理异化不同,歌颂的是顽强的生命力。着眼点不仅在控诉封建法西斯造成的人性异化,而且在探索正常人性复归的现实可能性。以实出虚,化实为虚,虚实相生。多了一个象征的层次,便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容量。这种手法运用得好,比平庸的写实更能鲜明有力地说明内在的真实。在《斩凌剑》里,卢沟桥的十一个桥墩也构成一个象征,却由于虚大于实,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艺术的变形,常常带某种必要的抽象。无论小说家如何标榜作品直接符合生活真实,他也不可能把繁复的生活拖泥带水地移到纸面。他必须剪裁、删除、选择、集中。文学概论告诉我们这是形象思维的典型概括过程,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抽象。在这种典型概括中,艺术家对事物的普遍本质的认识是与对事物的丰富个性特征的直接把握联系在一起的,忌讳任何苍白、稀薄的抽象化思考。然而,有时候,在保持所有这些鲜枝嫩叶的生动性的同时,却有必要来一点去除水分的蒸馏,一点艺术的抽象,取共性而撇去任何个性。例如《阳台》的开头,讲到为迫害红点子教授卖过力气的人有十来个,但多数是好人。“真把张三李四一个个写上去,那多不合适。就写一个我吧,打人是我,骂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种种坏事,都是我干的得了。可巧有的坏事,一个人三头六臂也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好?索性写‘又一个我’,‘另外一个我’,‘两三个我’,‘十几个我’。”地点呢?“还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说是学校还是机关怎么样?”就像《阿Q正传》开头那貌似“开心话”却大有深意的“考证”,最后只剩下一个“阿”字准确无误,这里唯有小说的主角,红点子教授决不含糊。
在这里把张三李四等等抽象为“十几个我”,把具体地点也一概略去,就把特定的“这一个”,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艺术的抽象把人物和情节从特定的地点和狭窄的“真实”里解放出来,使红点子的遭遇带有几分那一年代里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普遍的性质。同样,在《记录》里时间、地点、肖像描写、动作都全部略去了,只剩下一个无名无姓、盛气凌人、愚昧狂妄的审问者,和一个名叫曾一同的受审问的知识分子。这一可悲可笑可怖的审问就超越了具体的时空,而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真实性。在《神经病》里作家用张三李四王五来命名他的人物,也是有同样的用意在的。
林斤澜说:“我自己的东西不完全那么写实,但我喜欢写实主义的写法。”岂止是喜欢而已,林斤澜能够纯熟地写出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像《膏药医生》《开锅饼》《头像》《肋巴条》都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有个性的人物。有过素描写生的严格训练的画家,画起写意画来也许更能挥洒自如。非写实的成分也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是现实生活的升华、结晶,并不显得虚玄、缥缈、神秘。即使像《火葬场的哥们》这样的情节离奇的“口头文学”,林斤澜也能点铁成金,通过特定环境中人物性格、心理的逻辑,铺垫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因而艺术变形是为了追求艺术真实,内在的真实,是符合作家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与此相关的是作品中的主观客观问题。老作家孙犁在《读作品记》里写道:“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表面看来,林斤澜是一个冷静的,不动声色的作家,他的笔更像医生的解剖刀。其实,他的主观倾向相当强烈,只不过是用冰一般的冷峻包裹着罢了。这一倾向不是通过直抒胸臆,而更多的是从选材、夸张、集中——艺术变形中表现出来。艺术家是一面凸透镜,事物成比例的变形标明了他的“折射角度”——他的主观倾向。这一倾向直接的“可见因素”就在于他的语言风格,他的“语气”。
作品的“语气”表明作家对笔下人物、事件、气氛的评价,标出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就确定着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林斤澜以冷峻、嘲讽、诡奇的笔调,有意使读者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希望读者以挑剔的、紧张思索的目光,注视他笔下展开的一切。小说里所讲的,读者也完全应该参加进来,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改造、重新组合。就像《膏药医生》里听故事的青年人那样,不必执着于“非是非不是”。林斤澜的嘲讽语气又是他对历史的理性思索的产物,是对疯狂和荒诞的蔑视。无论《法币》里的反语,《问号》里的冷嘲,《神经病》里的幽默,都蕴含相当深刻的思想力量。虽然林斤澜说“这一段生活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也因此给描写带来了困难,好比这五味,以哪一味为主呢?不好调配”,但他还是着力去写出五味俱全中那难得的“酸甜酸甜味儿”。因此,他的小说,冷峻中有暖色,压抑中有力量感,经看,耐嚼。
“小说原是有各种各样的”
林斤澜小说的独特风格,他的艺术追求和创新,产生于对“图解文学”的深刻反思和再认识之中。
“图解文学”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产物,是经济主观主义和哲学唯意志论在文学上的对应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斤澜就记取一位前辈作家的告诫,晓得“他们那时搞写作,是从生活中自己去摸索、分析、评价才得出结论的。……只有你从生活中找到了最感动你的东西,才能表达出你对生活的感受,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之后,他又语重心长,多次讲道:“我们又往往不容易摆脱‘图解’二字,图解思想,图解主题,图解政策,图解工作过程,图解长官意志……”到了一九八〇年,他在积极深入农村生活,写他熟悉的农村题材的同时,又不无先见之明地提醒人们注意:“‘图解’这位神通,可不可以唤它回来?”“我们这些人以往在这头走的冤枉路多了,吃的亏大了,不免多操一份心,怕它唤之即来,挥之不去。实际在有些地方,它现在也还直撅撅地戳着呢。”
在当代作家中,像林斤澜这样郑重、严肃地总结“图解文学”的全部教训,对之保持高度警惕的,恐怕还不多。事实证明林斤澜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可以说,摆脱“图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图解文学”的根本要害,在于作家没有自己的“魂儿”。它带来艺术内容的苍白和抽象。它更带来对短篇小说艺术形式的直接危害:由于素材缺乏内在联系,结构必然松散无力;人物是政策条令的化身,人物关系既臃肿又单调;情节被冗长的过程取代,细节则琐碎地组成一幅黯淡的画面。多年来人们对于“短篇不短”的责备,对于公式化概念化的不满,只能是“图解文学”的直接后果。
回顾林斤澜写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还有生命力的那些成功之作,再考察他近年来的艺术探索,他对“图解文学”再认识的意义就更清楚了。与“图解文学”的千篇一律相反,林斤澜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我们很难将他的小说形式归类。他的小说总是从内容出发选择最适宜表现自己感情的形式。在这里,我们涉及了一个至今极少为人们所注意的题目,即短篇小说艺术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宏观发展。在本文范围内我们不能对此做出哪怕很有限的说明,我想仅仅指出这样一点:林斤澜小说艺术探索的一方面意义,就在于延续了鲁迅所开辟的现代小说绚烂多彩的艺术道路,探求多种多样的途径,以发挥短篇小说的艺术特长,来容纳日趋复杂多变的当代现实。
我们知道,短篇小说在西方是史诗和戏剧等宏大形式之后才兴起的体裁,在中国却是长篇小说等宏大形式的先驱。中国古典的长篇小说一直保留着“短篇连缀”式的结构,短篇小说则一直延续着有头有尾讲故事的程式。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起于并成熟于鲁迅的《呐喊》《彷徨》。鲁迅的二十余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创造了一个新形式。如此短制,却能表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内容,容纳如此广阔的时代画面,又无不具有完整、和谐、统一的形式美。中国古典的短篇小说的美学形式解体了。在鲁迅那里,有的是横断面,有的是纵切面,有的只是一个场景。有的多用对话,有的近乎速写。有的采用由主人公自述的日记,手记体,有的采用由见证人回述的第一人称。有的则用作者客观描绘的第一人称。有的抒情味极浓,有的却是强烈的讽刺。有的专析心理,有的带明显的思辨色彩。写实为主,又兼融浪漫和象征手法。
当今作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复苏鲁迅的多样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就短篇小说而言,它的作者正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相对凝练单纯的体裁与繁复庞杂的现实之间,存在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浩劫过后从事写作的新老作家,他们对生活的整体性认识尚未达到长篇小说所能容纳的高度,而巨大的历史内容和丰富的心理内容,用短篇小说来驾驭又有极大的难度。这就产生了两种趋向:一种是中篇小说的崛起,一种是短篇小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固守短篇小说的陈旧程式,就要冒把新的生活内容陈旧化、简单化的危险。为新的生活内容寻找适合作家艺术个性的新形式,就必须冒失败的风险,顽强地探索前进。由此产生了短篇小说领域内颇具规模的“风格搏斗”。王蒙是能够写“典型的”短篇小说的作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冬雨》,复出之后的《最宝贵的》,都是短小精悍的佳作。但是在这场“风格搏斗”中,他却另辟蹊径,倾向于写“那种虽写断面,却能纵横挥洒,尽情铺染,刻画入微的长而不冗,长得‘过瘾’,长得有分量的‘长短篇’”。他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林斤澜坚持的却是另一条,也许是难度更大,成功的“保险系数”更小的道路。那就是,在剪裁提炼当代现实、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心理内容的同时,坚守短篇小说简洁有力的艺术风格。
简洁,是林斤澜艺术风格中最基本的要素,又是他三十年小说创作中贯串始终的风格特点,更是他立足于民族传统来吸收现代表现的一个标记。在本文前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要素在主题锤炼、人物刻画、环境描写、表现手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种熔铸性作用:凝练到可用一个词概括却又无法用文字说尽的主题;用写意的白描手法夸张了性格特点的人物;省到了无法再省以至在抽象中“消失”了的环境描写。我们还会发现“简洁”在他的结构和语言方面所起的更明显的风格作用。简洁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理所当然的风格要求,但林斤澜对它的坚执固守却到了几乎是苛刻的程度。我们读他的小说时感觉到的某些冷涩、晦暗、糅合不匀净之处,就是这一“风格搏斗”的痕迹。是那大容量的当代现实在简洁的外壳中挣扎、沸腾、咆哮。是短篇小说的艺术特长在新的蜕皮中产生的疼痛和不安。
但是,林斤澜不是一个为风格而风格的作家。一方面,风格是“一种逐渐形成习惯的对于题材的内在要求的适应”(吕莫尔《意大利研究》)。另一方面,风格“只不过是思想的最准确最清楚的表现”(左拉《实验小说》)。写于一九七八年的《小店姑娘》《悼》《竹》《开锅饼》和《膏药先生》,既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格的延续,又是新的艺术探索的开始。似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提炼尚未达到新的高度。其中《竹》的字数将近三万,反映的生活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采用书信体双线结构,实写了革命斗争历史,虚写了“文化大革命”,人物和事件有传奇色彩,也有抒情性浓郁的象征。思考的深化是在一九七九年。《法币》《问号》《记录》《绝句》《微笑》五个短篇都只有四千字左右,却结构完整,内容充实,入木三分,正是作家独到的魂儿已提炼出来的标志。如《问号》只是一个场面,却写出了“最最最革命”中的“最最最恐怖”。一九八〇、一九八一两年,形式更加多样化,视野更加开阔,探索更加多方面。《酒言》借老队长酒酣耳热中一席肺腑之言,叙农村二三十年沧桑多变,是近年来描写农村变化的小说最短又最独具一格的一篇。写变化的同时又不回避新问题新矛盾,包含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辘轳井》分上下两篇,一亩菜园子里透出来无限绿意,二十多年世事浮沉中断而又续,小说不重情节也不重在人物刻画,却着力在抒情、意境上下功夫。《寻》也是一篇历史跨度二十余年的小说,像电影里的闪回镜头,山雨中一双粉红的雨靴,引出悲欢难诉的往事与严峻的现实相糅合,紧凑的对白里压缩了多少历史的心理的内容,你很难相信能为一篇五千字的小说所容纳。一九八二年的创作又有新的特点,《邪魔》《腾身》都把多种矛盾集中于一时一地,愚昧迷信、派性残余和新的唯利是图,旧矛盾新问题纠结着难解难分,展开富于心理深度的冲突,却把最有光彩的场面放到结尾,让不动声色,永难磨灭的崇高品性脱颖而出。“戏剧—小说”式的艺术结构,精彩的对白、独白、潜台词构成小说内在的紧张和美,无疑是林斤澜对当前艰难地腾身起飞的现实复杂性,有进一步深刻理解的艺术体现。
从上面相当简略匆促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林斤澜小说形式的变化极其多样,而且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力求最大限度的简洁和集中。简洁要求结构上高度紧凑,不是全景的浓缩,而是一个角度的透视,一个片段的截取。简洁要求精练的对话。林斤澜是从戏剧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这方面的经验于他大有帮助。他尤其喜欢把往事、回忆用精练的对白或独白道出,历史内容在口语中产生逼真的现实感,活在眼前人物口中的历史,因而也就是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作用的历史。简洁要求省去一切可有可无的细节、铺垫、过渡,有时在我们看来必不可少的环节也被略去了,猝然的中止常常使人摸不着头脑。简洁要求一以当十的细节,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拿掉其中一个就会显得不完整。但细节的多重暗示性常使我们感到小说内部过分拥挤。简洁要求重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使之鲜明有力,耐人寻味。林斤澜认为短篇小说要像体操运动员的表演,在三五分钟里,“一下子抓住人,最后给人一个印象”,因而要抓好两头。但有的结尾未免过于雕琢。
老舍说过:“短篇想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林斤澜的短篇是拼了命来作的,他的努力证明了:艺术地表现我们时代的复杂内容,表现我们当代人的性格心理,仍然可以做到短而充实,短而有力;在那些最见功力的篇什里,也能做到短而自然。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短篇小说的艺术特长,适应生活丰富多彩的侧面,适应作家的艺术个性,去写多种多样的小说。林斤澜说:“小说原是有各种各样的,我的意见是各路都可以产生杰出的作品。”“拿来主义好不好?好。翻箱底思想好不好?好。尖锐,厚道。清淡、浓重。热情奔放,冷静含蓄。大刀阔斧,小家碧玉。变幻莫测,一条道走到黑……都好都好,都不容易……”
林斤澜的艺术发展可能还会是“变幻莫测”的,他的艺术探索却不会停止。“有好心人规劝探索者,不如回头走先前的道路。否,这是生活的‘内里面’决定的,也是艺术的‘内里面’决定的。如果停止探索,还叫什么创作呢?老是轻车熟路,对作家来说,他的创作生命也只是‘夕阳无限好’了,或者‘停车坐爱枫林晚’了。”寂寞的探索者在写作时处境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困难,他缺少同伴的竞赛、切磋和反驳,他可能走冤枉路,从一个点岔出去很远又绕回来,他难免煮夹生饭,对作品的成功抱着相当固执却又不太有把握的愿望。然而,探索的路仍在延伸,延伸——探索者,青春常在!
1982年12月26日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1949年生。高中毕业后,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散文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