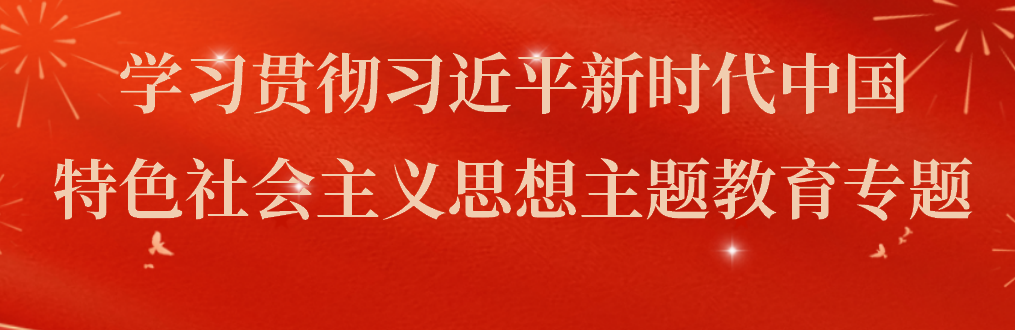在这么长时间的写作生涯里,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像所有去上班的这些律师和会计一样,反正到了点我就坐在我的写字桌旁边,我对写作这个事情有一种很平常的心态,那就是——我是靠写字来养家活口的。
我记得我跟王安忆有过这么一次讨论。她说,作家30%靠天赋,70%要靠后天的努力。我说我认为正好是相反,作家要靠70%的天赋,30%的努力。但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作家50%是靠天赋,然后我还要加入20%的职业训练。
职业化的训练不能给你天才,但是如果你有天才的话,它至少可以让你在使用你的天才的时候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使你的所有天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
我记得我在1988年的时候,刚刚出道不太久,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就被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发现了。他们看到有我这么一个军中的作家,初出茅庐,势头还不错,于是他们请我到美国去访问,我在美国看到了他们怎么样训练职业作家。
美国有一些写作中心,会邀请很年轻的作家在一起探讨,一起批评,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个个都是写作家、小说家,也个个都是文学批评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羡慕,因为当时虽然中国有一些作家班,但是他们没有给过一个作家职业上的训练和规范式的教育。
我回到中国以后,就下决心争取去美国留学。我去美国留学的这个经过是很励志的,一年零七个月就考过了托福研究生线,当时美国的研究生线是550分,我从一个只认识ABC的水平,到后来的577分,这当中受的苦大家是应该可以想象的。
我考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芝加哥一个私立艺术学校里的文学写作系。这个学校除了文学写作系,还有电影系、舞蹈系。我是文学写作系一百多年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外国学生,你可以想见,英文不是母语的话,是很难用英文来写小说的。当时系里也非常看重我的成就,比如我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全额奖学金。
我感到他们的训练方式是非常科学的。上课时,我们的同学都是坐成一个圈,12个同学,老师坐在中间,然后他就说,某某某,你出一个词儿。被点名的同学先出一个名词,然后老师叫第二个人接一个动词,接了一个动词以后他就说,用你想到的最最独特的一个词来让这个名词动起来。这样一种训练就是他告诉你什么能使文章变得非常有活力。比如说老师跟你说这里有个烟灰缸,然后让所有同学就用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东西,当场构思出一个故事来。调动你所有的感官,来把这个故事往下进行。
我觉得这种写小说的训练在美国是独一家的。为什么我现在写小说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这是跟我们学校的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写一个东西要有质感。这段文字你写出的一个场景,要有质感,最好还有触感,就是说六种感觉都有,六种感官都有。这种职业训练对我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因为它还有第一人称写作、第二人称写作、书信式写作、嘲讽小说、各种各样小说的体裁的训练。
老师说,我不能给你天才,但是如果你有天才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在使用你的天才的时候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使你所有的天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
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得到艺术硕士及写作学位(MFA)出来以后,明白了很多事情。比如如果你想转换一个视角,应该用什么转换,比如说用对话转换是最容易的,从一个女主人公转变到男主人公,或者从她的心理的世界转换到他的心理世界,其实是非常有技巧在里面,这个技巧学会了并不影响你的天才的发挥,那么你有天才也有技巧,所以写起来就省力一些。所以我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后,就大量将这种技能运用在后来的写作里,写出了很多作品。
我觉得很多中国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架起来,社会也把他架起来了,很快他就在一个不落地的生活当中。
在美国,任何人,作家也好什么也好,我自己感觉跟我全班同学一样,他们后来出去有写广告词的,有写剧本的,写什么的都有。我也跟所有的这些同学一样,变成了一个每天用写作来尽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责任。
我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命。比如我比较喜欢中国近代历史,对我们中国这一百年间发生的故事很关注,或者说我在写个人命运的时候怎么样映照了中国的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我想写,我这辈子好像不写就会死,就激情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就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是一个靠卖字为生的人。我喜欢这样一种职业的独立性,我喜欢它的自由,那种没有极限的自由。
比如说我写《陆犯焉识》,我花了很多的钱,去青海去体验生活,花钱去开座谈会,把劳教干部等请来。然后我要找人陪同我,我要找很多关系来了解这些故事,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
我这时候感觉就是使命使然,感觉到这些故事我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我就白活了,就这种感觉。
这次我给路金波先生出版的《老师好美》,也是在六七年前,姜文跟我说网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特别好,我说我看看去。一看我也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地震撼,但那种高中生的状态我完全不了解。我于是就去了北京的161中学,种种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一种体验。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到学校去,争取选一个高中去那么两三天,看他们上课,跟他们聊天、交朋友,在网上通信,了解他们的语言,进入他们的语言系统。最后这个功课确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从听到故事,到最后写出这个故事,再到今年出版,大概花了七年时间。
我是一个职业作家,香港人管作家叫写稿佬,一个写稿佬的生涯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