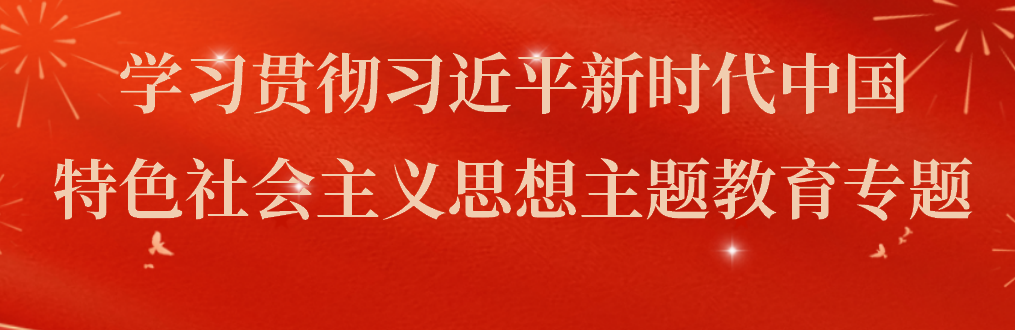在“历时”到“共时”的发展中,在中西文化有形无形的融合中,中国当代音乐既根植于传统又以不断突破,吸引一代又一代富有独立意识的音乐家置身于其中。当然,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要问,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国内外音乐发展交流成果的一个重要参照?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重要城市,近年来与国内外同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在日益开放、多元的文化艺术氛围中,我国音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总体呈现师生互换、学分互认、学者互访、合作办学、合作研究等内容,这种双向发展的模式已成为跨国流动交往的常态,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将“简单交流”变为“互相融合”,从而不断发掘探索与创新的学术潜力,使中国当代音乐步入了继上世纪80年代现代音乐发展高峰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7年,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在延续,且产生互向作用。
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和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共同在哈佛中心(上海)举行的中国当代音乐多维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会议的美方牵头人哈佛大学音乐系音乐理论学科带头人克里斯托弗·哈斯蒂教授以“中国当代音乐:无惧传统的现代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阐发让人印象深刻。“传统文化”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过去近百年中,这个话题已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而在当下,一个不断向我们逼近的“全球化”语境使交流对话成为中西音乐发展的重要依托,毋庸置疑,中西对话极大促进了彼此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中国当代音乐无惧传统与另起炉灶的取向,最终显露出“现代性”的文化精神。作为已渐形成一种更具整体性、系统化格局的中国音乐,其创作本身的不断成熟,带给中国音乐“现代性”的积极探索,其取得的成果也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之中,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许多实质性的意义建树,所以跨学科的问题也是当下文化交流延展后的重点。
当代作曲家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他们的创作往往有着中国化的处理与改造,这样的音乐语汇倾向使学者们获得颇为丰富的研究材料与理论实践。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汪立三钢琴曲《兰花花》、梁雷协奏曲《潇湘》以及罗忠镕运用序列技法创作的《涉江采芙蓉》等中国作品被许多专家置于案头深入研究。从内容主旨上看,这些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从经典之作到现代创新,既闪烁着西方现代文化的光芒,又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在中西的对话语境中以深邃、多元的发展体现了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历程缩影。而专家从创作、表演及聆听的角度入手,将视线投向了中国民族元素及西方技法的运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现当代音乐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与外界对话的契机,无论是“东瞻”还是“西顾”,最终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上得以延伸。我们不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现当代音乐中,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视界融合”,这是文化的选择也是发展的需要,而国际化的合作与交流作建立起的“对话”正对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国性”,还是融合西方现代精神的“中国性”,这并非与生俱来,亦非一成不变。一方面,人们不断加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对“传统”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一方面,则不断调整创作方式。可以说,中国音乐,无时不在“现今的视界”中被“此在”的人所改变着。在艺术的前沿上行走、追寻、求索的人一代接着一代,留下精神的影像、情感的印迹,他们和他们的艺术一直在成长和发展着。作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理论家,现今79岁的高为杰从上世纪60年代即注重融合西方作曲技法的探寻,埋下了本土与西方对话的胚芽。他的“非八度周期”人工音阶的音高结构系统可以说是基于传统音乐理论之上的新的作曲手段。在高为杰看来,要“力求创作出既具有‘意料之外的独特性,又在‘情理之中’的所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既富于感染力又合情合理具有严谨逻辑的作品。”而这样的思考同样浸润于后辈的创作历程中。作为60后及70后的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的贾国平和姚晨根植于东西方的音乐传统,又充分发挥了当代作曲技法的开放性。如果说贾国平的音乐创作是强调现当代音乐结构的理性特征,那么姚晨则对音乐语言的“临界”地带进行哲思的感知。无论是哪种方式,作曲家们都在不同文化意味的音乐语言之间进行对话,正如哈斯蒂教授所言的“中国当代音乐:无惧传统的现代主义”。中国当代音乐的进程,其创新与发展打破了时代的隔阂,显露出“现代性”的无惧传统的进步。
文化的差异增强了中西对话的意识,其展现出的“视界融合”也带来了双方思维碰撞的多维研究。多维研究需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元,打破中西方的二元对立,保持一种开放的对话意识。让多维研究的“对话”共在,这也正是中国当代音乐发展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