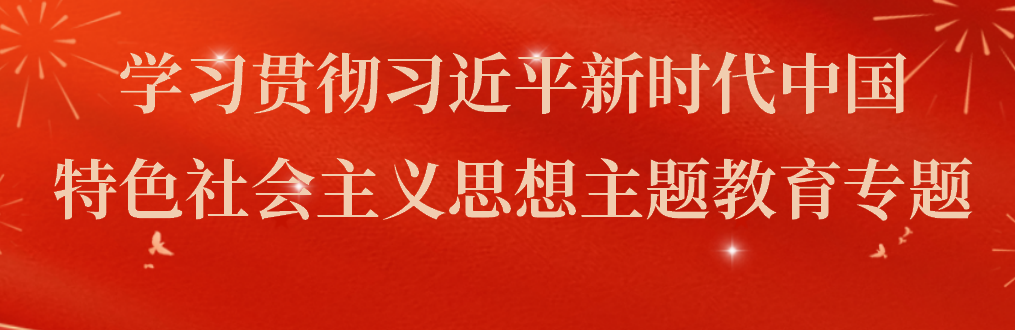城市文学的很多形式秘密,都藏在城市的地理学之中。现代城市中,街道是最普遍、同时也是最早被作家书写的空间。早在19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在美国刚刚兴起的时候,爱伦·坡就开始在街道中虚构文学故事了(《莫格街凶杀案》《人群中的人》)。之后,他远在巴黎的精神密友波德莱尔继承并发扬了他对于街道的好奇与着迷。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化身为巴黎街道上的文学游魂,第一次将巴黎光怪陆离的街道,提炼为现代诗意的发生学场所。路灯、橱窗、垃圾桶、拾荒者、妓女、交臂而过的陌生妇女、死老鼠……一切街道上的人与事物,哪怕肮脏、狰狞、丑陋、凶恶,皆可入诗。这是石破天惊的写法,自此,波德莱尔找到了他的文学产房。现代文学这个怀在波德莱尔肚子里的怪胎,在巴黎街道上分娩了。
自爱伦·坡与波德莱尔之后,街道开始成为现代文学繁衍壮大的根据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大街,巴别尔的敖德萨街道,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莫迪亚诺的暗店街……中国当代文学中也不乏后继者:苏童的香椿树街,金宇澄的上海街道,路内的花街,一直到新近的双雪涛的艳粉街、王占黑的小区街道。街道成为滋生城市叙事的宝地。
一、街道的空间分析
现代城市中的街道,是由水泥、砖头等工业建材构成的开放性空间,是人与泥土之间的障碍物。如一堵隔开婴儿与母亲的高墙,街道造成了人与土地、自然的隔离,同时强制古典(素朴)文学断了奶,让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街道的出现,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文学形式的革命。
土地与街道是两个可以纵向对比的空间概念。土地是乡村生产的固定场所,而街道是因货物(商品)交换而出现的流动场所,不承担生产的职责。生产的功能,使土地天然就是“留人”的,需要人长久地踩在泥巴里,播种、锄地、施肥、收获,积年累月,最终在土地上安居乐业。而街道天然就是“赶人”的,做完了买卖无法继续获利的人,绝对不会在街道上长久逗留。所以,土地有连续的历史。因为人是土地的主人,人的世代定居,保证了历史信息的积累、保存、更新。而街道是没有连续历史的,因为街道没有主人,只是一个流动人口暂时的聚集地。人来人往,造成了信息的流失、损坏与烟消云散。
居室与街道是两个可以横向对比的空间概念。居室是指经过合法租赁或购买,成为居住者暂时或永久住所的封闭性空间。居室是“私有”的,街道是“公共”的。居室是城市居民不动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资产。而街道是城市的基础交通设施,是公共资产。因此,居所属于“个人”,街道则属于“人群”——“大街属于人民”[1]。在现代城市中,拥有街道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只要腿脚麻利,出门便可实现。而拥有居室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大事。居室是证明自己城市人身份的证书。对于坐拥宅院的城市居民而言,街道是一个廉价的、透明的、毫无隐私性可言的“低等”空间。也就是说,在空间的权力等级中,居室高于街道。
二、街道的叙事学分析
在现代城市形成之前,叙事更偏爱居室经验。比如《傲慢与偏见》的乡村聚会,《呼啸山庄》中的山庄生活,《安娜·卡列尼娜》当中的贵族舞会。当然也包括最初的侦探文学(《失窃的信》的客厅)、科幻文学(《弗兰肯斯坦》的藏尸间)。现代城市诞生之后,叙事开始移情于街道。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地下室手记》,卡夫卡的《城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叙事的现代性转变,就发生在现代城市的街道上。
现代城市的大街,要比私人居室更容易滋生新的叙事。一方面,街道比居室宽敞、开放得多,是典型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经验的“转折点”:是乡村人和城市人相遇的地方,当权者与无权者相遇的地方,富人与穷人相遇的地方,男人和女人相遇的地方。异质性人群的碰撞、交会、渗透的时刻——也就是巴赫金所谓的“危机时刻”,本雅明所谓的“震惊体验”,可以化合出新鲜的现代经验。而城市的居室,窄小而逼仄,同时由于封闭性而拒绝了与他人的频繁交往,让独居者沉入了一种凝滞的“独白状态”。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独白式封闭式表述”[2]是诗的状态,而不是小说的状态,是反叙事的。而且,在寄快递、叫外卖、填写住址等时刻,居民感受到的居室,不再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实体,而是一个萎缩了、抽象了的编号。这种孤独、凝滞、窒息的体验,十分不利于叙事的运动,甚至可能扼杀叙事。
另一方面,街道比居室更加神秘莫测,有一种叙事所深爱的隐蔽属性。居所看似私密,但记录在案的住址与翔实的身份信息,早已将公民的信息暴露在外。街道看似公开,却有一种天然的遮蔽性——“在这里,大众仿佛是避难所,使得这类脱离社会的人免遭惩罚。”[3]。除非遇到特殊情况被查身份,否则即便一个越狱的重刑犯走上大街,也不会有人因认出而尖叫——在稠人广众中,个人反而是隐形的。这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个人,是现代叙事所迷恋的主人公。总之,如果说街道是“现代叙事的产房”,那居室就是“现代叙事的墓地”,或者说“经验的墓地”[4]。街道叙事对于居室叙事的超越,实际上是反资产阶级的叙事,对固化了的资产阶级叙事的超越。
街道在叙事中的功能,往往不是充当叙事的终点,而是充当叙事的起点与叙事延宕的场所。充当叙事起点,因为街道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一次擦肩、一次对话、一个眼神,就可以开启叙事。这种一次性的谋面,作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震惊事件,极容易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发育出戏剧性故事。因为“震惊事件”让时间飞逝的街头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凝视”。在这种凝视之下,庞德体验到的模糊的街道——“人潮中这些面容的忽现 /湿巴巴的黑树丫上的花瓣”(罗池译《在地铁站》),立即转化为波德莱尔所念念不忘的清晰的街道——“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新生的,消逝的丽人,/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钱春绮译《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麦克尤恩的《蝴蝶》便是一个由街道开启叙事的典型。这是一个流浪汉猥亵并杀害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女孩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开端,始于二人在街道上偶遇后,小女孩充满天真与好奇的搭腔:“你身上有股花香。”[5]
充当叙事铺展和延宕之地,得益于街道天然的迷宫形态。尤其是巴黎、爱丁堡等欧洲城市,街道走向的混乱、建筑群的高低起伏,令街道出现了数不清的“曲折”。“曲折”带来了空间纷呈的变化。如此一来,在街道上行走或行驶本身,就成为一种叙事展开过程。比如乔伊斯的《阿拉比》,在叙述小男孩“我”在街道上所见的空间变化的同时,也写出了“我”渴盼赶到阿拉比集市的焦急心理,以及被爱意驱使的强烈虚荣心:“我紧紧攥着一枚两先令银币,沿着白金汉大街,朝火车站迈开大步走去……我在一列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找了个座位。火车迟迟不开,叫人等得恼火,过了好久才慢慢地驶出车站,爬行在沿途倾圮的房屋中间,驶过一条闪闪发亮的河流……”[6]
三、街道的文学形象
有两类文学形象经常出现在街道上。一类是作为城市移民的“游荡者”,一类是作为城市土著的当地常住居民。二者都不是英雄或传奇人物,而是“市民社会的史诗”(黑格尔语)的主人公,是“低模仿人物”,或是“讽刺型人物”(弗莱的分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稳固的居室,后者则恰恰相反。
“游荡者”通常是一群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身份不明的边缘人:比如流浪汉(《小癞子》)、霸占街道的街头混混(博尔赫斯《玫瑰色街角的汉子》)、革命家或密谋家(雨果《九三年》)、从现代工作制度中逃离的上班族(霍桑《威克菲尔德》)、记者或侦探(莫迪亚诺《暗店街》)、欲望型青年(司汤达《红与黑》)、妓女(莫泊桑《羊脂球》),以及本雅明提及的现代艺术家们(现代诗人、摄影家、行为艺术家等)。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中,“游荡者”几乎全部是一群离开了乡村却又无法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人、学生与无产者。他们通常是一批寻找买家的劳动力,一种反复被抛售的廉价商品。他们最关心的是饮食男女的基本问题,以及如何克服不适感,尽快融入城市的身份转型问题。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编制,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不受现代工作制度控制。但因此也没有城市福利的保障,生活在摇摇欲坠的脆弱的安全感之中。为了吃饱穿暖,他们日夜颠倒,将城市土著居民的闲暇时间(下班、休息日)变成了自己的工作时间。
相比于“游荡者”,城市土著的生计问题基本得到了保障。他们或是有房有车有编制有户口的有产阶级(“游荡者”的第一阶段奋斗目标),或是有房有户口、更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退休老人(“游荡者”的第二阶段奋斗目标)。他们关心的不再是生计问题和身份转型问题,而是孤独、冷漠、疏离等精神异化问题,与如何保住城市人身份的问题。前者偏激进主义,是“打江山型”的人物,比如于连。后者偏保守主义,是“坐江山型”的人物,比如欧也妮·葛朗台。
“游荡者”常常没有固定居所,甚至要露宿街头。他们身上聚集了大量的叙事可能性。他们涌向街道,是为了将街道变成自己的居室,遏制叙事的漫漶与频繁暴动。这是在努力“无中生有”——“街道成了游荡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对他来说,闪闪发光的珐琅商业招牌至少是墙壁上的点缀装饰,不亚于一个有资产者的客厅里的一幅油画。”[7] 城市土著虽然有固定的居室,但过于封闭、狭小的居室空间,功能稀少,无法满足他们对于各类型的空间的渴求,叙事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他们走上街道,是为了和人群相遇,发生联系,发生故事;为了让街道空间成为他们的广场、公园、歌厅、舞厅甚至健身场地。换言之,他们是要将街道变为个人居室的扩充,用街道上的“对话”拯救居室中的“独白”,为叙事做心肺复苏术。这是在努力“变小为大”。
“游荡者”与城市土著这两类文学形象,虽然涌上街道的起因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将街道这个人造的“陌生空间”,转化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空间”,类似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更清晰一点表述是:他们共同在城市中,建造一个小小的“乡村”。包含于其中的诉求包括:改变城市规划的严格界限,减缓一切向“秩序”看齐的进程,恢复人与人、空间与空间的亲密联系,弥合居室与大街——也即乡村与城市之间迅速撕开的巨大伤口。这一点在王占黑的新作《街道江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她不遗余力地刻画一个小区街道上的看门人、菜摊摊主、流动小贩、剃头匠、孤寡老人,最终把城市的一条街,变成了一个“游荡者”与城市土著携手建造的“共同体”。
“游荡者”与城市土著,看上去一方是围城之外的人,一方是围城之内的人,在资产、身份、精神追求上有天壤之别。但在精神深处,双方都怀着深厚的乡土文明情结。这个情结就是—在城市中重建乡土的熟人乌托邦。这是他们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失根与精神漂流的解决方案。这表明,他们对于城市的陌生社会与人造景观,本质上仍然是不适的。在涌上街道的时刻,他们分别拆毁了各自“身份的城墙”,以“街道居民”的共同身份,成为暂时的“亲人”——这种亲密,不是乡土文明那种来自“相同血缘”的亲密,而是来自“相同地域”(同一个街道)的亲密。将血缘联系变为地域联系,重建一个乌托邦,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精神秘密。
除开张爱玲、施蛰存以及当代《长恨歌》《繁花》等城市文学作品,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城市文学,还并没有在中国的街道上分娩。中国城市文学当中的街道,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乡村黄泥大街的延长。它召唤的不是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欲的现代人,而是锣鼓队、秧歌队与下山的牛羊。当代中国城市在等待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必须对新的城市经验(可见的街道和不可见的信息迷宫、妓女一样的商品、梦游一样的人群等)保持足够的好奇……必须单枪匹马轻装上路,而不是成群结伙;必须对漫漫无期的迷宫之旅保持足够的耐心;必须培养对不可捉摸的人脸的兴趣……必须真正热爱城市这个迷宫;必须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认同’这个时代”[8]。
参考文献:
[1][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11页。
[2][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3][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4页。
[4]张柠:《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5][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6]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孙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0页—31页。
[7][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0页。
[8]张柠:《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