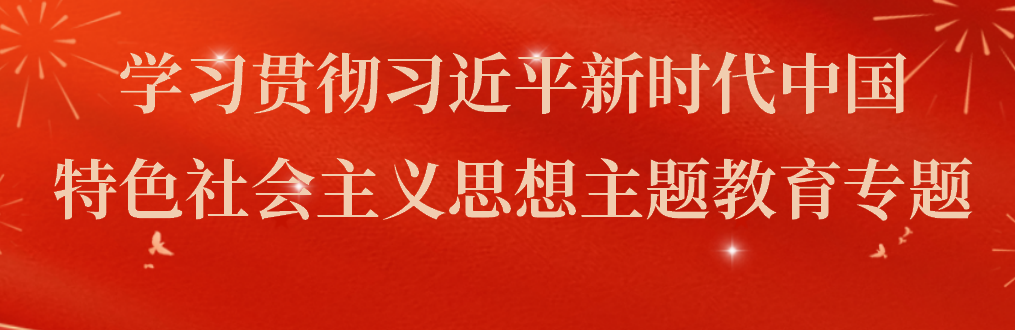春游陶然亭
文/乔 叶
一
春光和煦日,去游陶然亭。
忆起来,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也才20多岁的年纪。这些年总有些缘故,每年都会往北京跑几次。那年代还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从豫北老家到北京,我常坐的火车,除了K字头的算是快车,其他的就都是晃晃悠悠逢站必停的绿皮慢车了。绿皮慢车总会停靠在永定门附近的北京南站。从南站坐上公交,七拐八拐的,就会路过陶然亭公园。透过车窗,看着公园里隐隐露出的亭台楼阁,绿树繁花,就会涌出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进去看看才好呢。
不曾想到,这个心愿得以满足,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不过,此时看也有此时看的好处,人虽然已不年轻,对于看风景却多了些心得。年轻时候到底还是单纯浅薄,看风景就是看风景,有时候甚或连风景也顾不上看,就只顾玩自己的,更谈不上去体悟风景背后的风雨沧桑。如今年长,懂了些事,但凡要去人文掌故积淀之地,都会做点儿功课。否则只在风景的表层匆匆浏览,于内并无所得,就觉得空虚且愧怍。“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的千古感叹,窃以为也可以借用过来作为我等中年人看风景的延伸:这个地方,曾经驻留过什么人的身影,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爱恋,他们的热望,我都想去有所贴近和体会。换句话说,风景自是由人去看,可从根子里讲,看风景也是在看人——那些肉身不在却精神长存的人。你想想,去成都草堂是不是为了看杜甫?去滁州醉翁亭是不是为了看欧阳修?去杭州西湖,自然是为了看苏轼看白居易看林和靖看岳飞啊。
这次去陶然亭公园,怀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陶然亭公园,顾名思义,自然是先有亭后有园的。但比这亭更有历史的其实是慈悲庵。慈悲庵创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庵内有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等。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年(1663年)曾重修慈悲庵,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时,大约是因为离这里不远,便常到此游玩。来得多了,赏景入心,就在慈悲庵西侧建了亭。亭建成后,取名“陶然”,是采撷唐代诗人白居易名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共君”的本质是邀友,江藻常邀友人以及友人之友人到陶然亭内欢聚。主雅客来勤,久而久之,这里便嘉宾盈门,诗文不断,佳句时新,传扬开来,陶然亭乘着诗香文韵,声名很快便大过了慈悲庵。而到了现在,陶然亭和慈悲庵已然被岁月凝结在了一起,难以分开。
今天来陶然亭,当然不是为了江藻。我想探访的那些人,在100年前,他们也曾一次次相聚在这里,为了他们赤诚炽烈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想,其实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很近,近得似乎从未离开。
二
票是在网上预购的,通过“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两块钱一张,惠民得很。在来实地之前,我也已经在陶然亭公园的网站上进行了一次虚拟游,所以这次虽是初来,却颇有些故地重游之感。

彭华竞 《陶然亭》 220X200cm 国画
进的是南大门,迎门便看见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在树枝间穿梭欢鸣。已经出了正月,“龙抬头”的二月二也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时节回暖,正值初春。迎春花或在路边,或在坡上,或聚拢,或单株,绽放出一簇簇金黄。柳树的枝条丝丝垂垂,轻飘于微风之中。“绿柳才黄半未匀”?其实已经黄中偏绿,且匀得很了。枝条上面还有红灯笼高挂着,年气混搭着春光,娇艳悦目。
游人很多。看来游春踏青,此地就是北京的上上之选。有穿羽绒服戴棉帽子的,有围着轻薄丝巾的,更多的人穿着运动装和休闲服。有步履缓慢的老人,也有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有姐妹般的少女娇俏欢笑,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情侣携手而行。当然也有我这样单个儿的,不过我也不寂寞。这么多人不都是伴儿吗?认不认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园里有四片湖,东湖,西湖,南湖,最西侧的那片叫荷花湖,想来是有荷花的。迎面这片碧波既然离南门这么近,应该就是南湖了。据说早在辽金时代,这一带还是城外郊野之地,水源充沛,溪流密织,到处可见河池湖泊。这一泓清水是不是就是往昔水乡的印证?还据说当时此地就有苇塘,苇塘中就有岛屿,岛上有土丘高耸。隔着南湖眺望,正前方的岛就该是当时的岛了吧?苍松翠柏掩映的高处,隐隐可见有灰墙飞檐的建筑,那应该就是慈悲庵和陶然亭的所在地了。
便直奔而去。到了地方才看见幕布围挡,围挡上贴有告游客书,说正在修缮,过些时日才能开放。我不甘心,仔细察看,居然发现有一处围挡错开了一条缝,能容人进出,应该是用来输送建筑材料的。静悄悄的,也没人拦着。那我就不客气了,便见缝插入,进到墙内。不过里面并没有什么沙土砖石,很是干净利落,应该是修缮即将完成。这是否天赐良机,允我先睹为快?
拾级而上,便看到了那棵大槐树。槐树下的照片已经摆放到位,正是我在资料上看到的那张。一旁的介绍文字相当简短: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仁学社在京部分成员在慈悲庵大槐树下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不用点明“左四”,我也能一眼认出他。这个器宇轩昂的俊朗青年,长棉袍,黑短褂,短发,还微微袖着手。也是严冬了。槐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一共10个人,每个人都穿得很厚。
介绍简短,照片简薄,但这至简的文图背后,是何其跌宕的时代风云。据史料记载,晚清时的慈悲庵和陶然亭已是逐渐荒芜,尘音寥落,这种情状却恰好易于避人耳目,利于谋事。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在此计议过变法维新。1920年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先后在此留下了活跃的足迹,辅仁学社是1913年由湖南长沙第一联合中学部分学生组建的社团,社团成员思想活跃,积极参与时政。后随着诸多学社社员进京求学,社团活动的重心也逐渐迁到了北京。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在京的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邓中夏等在慈悲庵内共同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留下了这张珍贵影像。
对这个地方,毛泽东应该是记忆深刻的。1950年底,他由罗瑞卿陪同,来陶然亭故地重游。那时此地仍是一幅残败景象。据说他在慈悲庵前的老槐树下追忆往昔,感慨万千。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了民工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清理和扩展,陶然亭连同周围水域被辟为公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兴建最早的一座园林。公园的名字也是因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以现在的标准看,它的像素岂止不高,简直可以说是太低了。人面都有些模糊,只能看清楚基本的轮廓。毕竟从1920到现在,这照片已经拍下100年。不过,也还是幸亏有它。有它就有了“立此存照”。更何况主要的印记还在。有些东西,不但不会被时间磨损,还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越来越明亮和清晰。
三
对于李大钊先生,这里也应该是一处特别之地。据史料记载,1920年夏,周恩来与觉悟社成员和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等进步团体20余位代表也在此集会,讨论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等问题。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团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这一主张有效促进了社团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团结统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夏,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新葬于陶然亭畔要为夫人守墓为名,租赁了慈悲庵南房两间,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此参加会议。李大钊先生身故后,友人曾提议将他葬在陶然亭,因陶然亭是他最喜爱的游憩之地,但最终此提议没能实现,成为憾事。李大钊被葬在了香山万安公墓。
合影里的左五应该是邓中夏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简介在网上搜就可以搜到,读起来可谓惊心动魄: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那时李大钊先生在北大任教,在其影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带领讲演团到街头演讲,增强民识,启发民智。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推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主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他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3年2月,他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并在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雨花台就义,年仅39岁。
左六是罗章龙,他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也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于1995年去世,临终前的心愿是也想葬到万安公墓,和李大钊先生在一起,后来得偿所愿。
我的眼睛在他们的脸上一一聚集,停顿,行注目礼。虽然不能将他们的面貌和姓名一一对应确认,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厚重大书,值得一读再读。
进到作为展室的厢房里,正对面也是这张照片,与槐树下的照片不大一样的是,这一张做成了颇有韵味的水墨画风格,我便上前翻拍。
一个年轻的工人正在刷地面,他埋头苦干着,专心致志。
“这工程快结束了吧?”我问。
“是啊,快结束了。”他抬起头,擦了一下汗。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给地砖刷保护油。”许是觉得我有些懵懂,他又解释,“像给木地板打蜡一样。”
“哦,这么认真啊。”
“这么重要的地方,当然得认真啦。”
……
看我从各个角度翻拍这张照片,他又告诉我,这棵槐树不是100年前的那棵啦,是新槐树,补栽的。
我夸他很内行,并谢他告知。他羞赧地笑了笑。其实这个我知道。资料里说,现今的槐树已非原树,是1979年选近似株形补栽的。不过,在我的意识里,是不是原来的槐树并不那么要紧。新树自有其意义。此槐树彼槐树,从根系上来说,就是一株槐树。当它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就已经有充分的资格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是吗?
就像这正在修缮的房子,它雕梁画栋,彩绘明丽,看起来就像完全是新盖的一样。就物质意义上来讲,它早就不是原来的了,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只要那些人的足迹曾来过这里,那些人的心脏曾在这里鲜活地跳动过,那些人的声音曾在这里生动地回荡过,那么,他们就赋予了这房子历久弥新的坚实意义。
四
慢慢行来,慢慢欣赏。到处都是曲径通幽,却也会让我不时迷路。迷路也没关系,再拐回去就是了。
高君宇墓就在这里。那就去看看他吧,还有他的石评梅。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简称高石墓。在他们的石像周边,有几树梨花正开得洁白似雪。他们的名字活在这段如火如荼的历史中,居然也已经百年了。早就听闻过他们的故事,可这次细读资料才约略明白100年前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革命与恋爱”:高君宇尚未挣脱旧式封建婚姻的捆绑,有意却无自由;石评梅正在经历新式恋爱造成的伤痛,心动却也情怯。也就是说,互相爱慕的他们竟然没有敞敞亮亮、痛痛快快地谈这场恋爱。这两个星星一样璀璨美好的青春灵魂,他们的烈焰竟然是在生命之火将熄之时才置之死地而后生,才开始燃烧,才长明至今,且被岁月和历史锻造成了悲欣交集的双子星座。1965年,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在“华夏名亭园”这个园中园我也流连了许久。园名是启功先生题字。
1989年此园荣获全国设计金奖。园内集中仿建了六省九地的名亭,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这些亭里,一多半我都到过实地,这次能够集中地再赏一次,仿佛穿越了一般,也是有趣。
还邂逅了名为“江山亭聚”的中国亭文化展,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了,看不得展了。展板上的一小段介绍倒是很有意思,摘录如下:张宣题倪瓒画《溪亭山色图》诗云:“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杪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
好一个“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
云绘楼和清音阁也是我想要看的。据史料记载,云绘楼本是皇家园林建筑,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原在中南海内东岸,双层楼廊,玲珑秀丽,是当时皇帝登楼观太液池时吟诗作对水墨丹青之处。1954年因施工需要拆除,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这组建筑结构和风格独具特色,建议保留,周恩来表示赞同,并和梁思成一起到陶然亭亲自选址,把这组建筑完整地迁建到公园的西湖南岸。这么算起来,它们“搬家”至此居然也有60多年了。
一路向东,看到一块巨石上镌刻着四个大字:潭影流金。面前是一片湖水,可以算作是潭,那么流金流的是什么金呢?再往远处看,有一片树林,像是银杏,便走上前细看。一位大叔正用背撞击树干,听我询问,便用浓浓的南方口音应答:就是银杏。
是银杏,这就对了。想来到了秋天,树冠上的枝叶相互交错,叶叶烁金,可不就是流金的金?有几棵还长得还挺粗大。银杏树是慢树,能长得这么粗大,至少该有100年了吧。
还有什么植物呢?对了,还有海棠。一大片的西府海棠,已经打了嫩苞,有了绿意,再过些天肯定美不胜收。还有金银忍冬,也是一大片。还有很多松柏,还有很多榆叶梅,还有很多大槐树……
踱至一个小山坡下,有几个孩子在跑上跑下地冲锋打仗玩耍。桃花红杏花白,衬着松柏,深色深,浅色浅,明媚的阳光中,深浅叠加,分明如画。玉虹桥边长长的健身步道上,有几个人正在疾奔,居然都是短袖。也难怪,“二八月,乱穿衣”嘛。有几块空地上画着一些白线方格,是用来打羽毛球的,果然也有很多人在打。场地现成,球具自带。有带网的,把网一扎,俨然很正规的样子。也有没带网的,只带着拍子和球来,也能打得不亦乐乎。不期然间,我还听到了祖孙两个的对话,是奶奶在跟小孙女讲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规则区别。奶奶说,羽毛球不许落地,乒乓球必须落地。孙女分辩说,乒乓球不是落地,是落台子上。奶奶宠溺地说对对对,你说得对……
“拂面微风柳万丝,春光犹似去年时。幅中折角无人识,醉依江亭唱竹枝。”不知道这是谁的诗,刻在路边的石台上。我在手机上查了又查,居然查不到。索性放弃了。是谁写的也并不那么要紧吧,在我的想象中,他就是一个春游陶然亭的人,和我一样。
快出门的时候,听到有刚进来的人问另外的游人:“请问陶然亭在哪儿?”
被问的是一群人,都笑了:“这就是陶然亭嘛。”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陶然亭中的陶然亭……”
所有的人都遥遥地指向那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