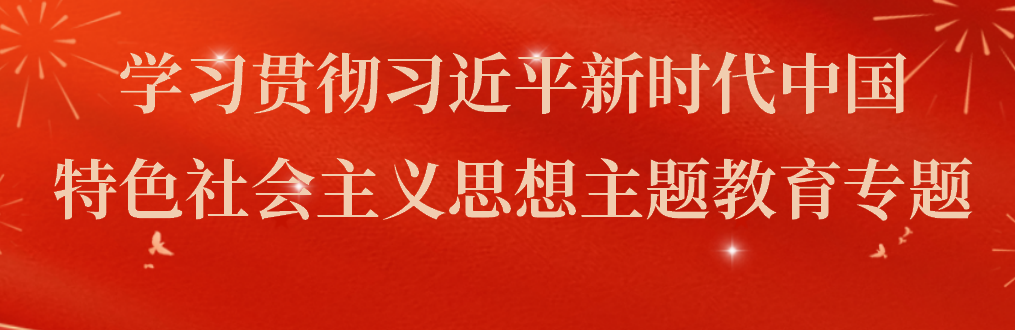红楼第一人李大钊
文/徐 剑
将近清明了。北方陡然惊现倒春寒,云压城低,冷雨一夜锁京畿。他要回云南去给老母亲上坟,离京前,却有一事未了。百年一日写红楼,真正红楼楼主,百年第一人,非李大钊莫属。然而,谒过红楼,转过故宫东北角楼,还有三个地方要去,东交民巷 29 号、31 号俄国使馆旧址与西侧兵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前者,为李大钊先生当年的避难和被捕之地,后者则是他的殉难之地。
天若有情,清明前的苍穹,总有几滴天泪落下,为众生,亦为死去的英魂。从沙滩红楼去东交民巷并不远,沿着护城河走过去,东边一河绕宫墙,先入北池子,一路王府至尊,雕栏玉砌,雄睨众生。而到了南池子,护城河之外,便是东华门了。
红楼百年第一人,他想到了94年前的天气,也像今天一样吗?
彼时,北京城郭天空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了一阵春雨,天为君哭啊。幽燕之地,过了清明节后,会突然变天,变来一场倒春寒,迎春花、白玉兰、西府海棠开得正盛时,蓦地,遭遇一场寒雪,或者一阵冷雨飘过。
李大钊走过来了,着一袭棉长袍,头发被狱卒剃光了,朝着绞刑架走了过来。那照片,看得人心碎、心痛。他是何等儒雅高尚之人,受如此奇耻大辱,蹒跚复蹒跚,铁镣是取下来了,可是那哐啷之声,是环佩之声,还是风铎独鸣,仍在身后回响。他望了望天,眼神有点黯淡,那副常戴的金丝框眼镜不见了,不知丢在何处。是他们将他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里架上囚车那一刻,还是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待的20天里,他们将他折磨成这个样子?
不忍凝视,一朝沦为“囚徒”。“北李”在他的心中,风采依旧,这种神采定影在了国民党一大闭幕式后,李大钊与孙中山同步走出大会时的照片。那一瞬间,是李大钊的灿烂时刻,步履轻捷,气吐芳华,风神华采光耀九州。因此,李大钊的形象,显影在一个少年心中就是黄河泰山。那是何等气魄,浩浩汤汤,不择涓流,故能成其为阔;那是何等巍然,不择土壤,故能成其为高。可是这一个时刻,泰山将崩,大海还会海啸吗?!
李大钊就要走了,步履从容朝着绞刑架走了过去。那是一种刚从法国进口的西方刑具,一根套绳,系成一个活扣,挂在一根横木架上,从天上往下看,那绳索是一个句号;从地上往天上看,那绳索是一个问号。
天问!守常一直在上下求索,在问天,在问黄土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泱泱我中华,怎么会衰落、积贫积弱到这个地步?半个多世纪了,国家和民族濒临危亡的边缘。从老家乐亭考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辆马车在将要秋收的道上,轧上两道深深的车辙,他在思考,在叩问,是谁将一个伟大的民族推向如此不堪的境地?那时已是大清末世,天津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一个个北洋大臣在此长袖广舞,练水师,练新军,教官请的都是洋人。他读的学校便是这场洋务运动的落果。是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洋人之技。可是气吞江海的北洋水师,从大清学童就开始了中国海军的深蓝之梦,龙旗飘飘,30年一梦冰与火,最终折戟沉沙,完成了悲怆的海葬。洋枪洋炮的小站练兵,一支支新军不过是皇权政治角逐的私器,不成国器,却成国妖,最终挽不住帝国的既倒,大殿天倾一角,灰飞烟灭。后来,民国了,可“民国”又怎么样,依旧民不聊生,依旧兵燹遍地,北京政治舞台上,这拨起家于天津的北洋军阀野心不泯,有枪便是北京王,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京华烟云”。从袁世凯称帝始,北洋小站系不断地在北京变换大王旗,直奉之战、中原大战,一场场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啊。1913年,先生从天津登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放眼东亚风雨,明治维新让日本找到一条图强之道,他有机会接触到日本社会主义者,读到幸德秋水、堺利彦著的书,开阔了他的视野。1916年他回国了,随后涌来的新文化运动,他投身其中,成了主将之一。但是,真正给他强烈冲击的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这是庶民的胜利,他为此欢呼雀跃。后来,他在天安门演讲中喊出了普罗大众的心声,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庶民的胜利”。随后,他在1919年 1月第5卷第5号《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堪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过后,那个夏天,他蛰伏于老家乐亭,写下了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圭臬《资本论》入手,从商品的属性说起,直趋剩余价值理念,唯利是图是资本家嗜血之好,最后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移入社会主义组织,根据这个预见,断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就是阶级斗争。而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篇万字雄文,洋洋洒洒,在1919年10月《新青年》第6卷第5、6 号上发表,标志着他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历史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黑夜沉沉的中国天幕上一个个问号拉直了,让一个个天问最终找到了历史性的答案。百年以降,一代代中国精英的探索都徒劳无功,他们或代表王朝,或代表皇权,或代表自身的利益集团,从没有一个人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从鸦片战争起始,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仁人志士,血沃中华,可是所有探索都半途而废。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一场巨变,结束了千年的帝制,在中国大地上立起了共和的旗帜,但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成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失败了,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了三个月,胜利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据为己有。天降大任于这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政治精英,他们或世家或寒门子弟,却都熟悉这块大地,植根于劳苦大众,探索的是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以及图强之道。中华民族的崛起重任,义不容辞地落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肩上。在“北李”心中,已经烙印了一个不泯的信念: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劳苦大众,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真的要流血吗?一个句号落下了,难道这个句号就是一个人生的死结吗?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现在,恰好八年,八年一梦京华烟云。五四运动落幕后,一辆马车碾着冬日的阳光,送走了陈独秀,从此“南陈北李”相望京沪,携手建党。维经斯基来了,马林、尼克尔斯基来了,俄乡来客,只是帮助,只是催生,关键还得靠自己。他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北大为阵地,通信会员遍及京、津、鲁等地,随后是1920年夏天,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成立,虽然一波三折,但是与上海形成呼应。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未去,派了他的学生与会。中共一大之后,他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先后任区委委员、委员会的书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依旧没有出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 5 位中央委员的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中共三大、四大,李大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了中央决策层。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时,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开始也想不通,与马林一场长谈,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只有参加,才能发展自己。有了执政资源,才能壮大自己。1922年8月,在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的“西湖会议”上,李大钊虽不是执行委员,但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与会人员中仅次于陈独秀的重要人物。面对大家对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都不太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他最早出来说,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态度”。
此后,李大钊奉命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2年8月至1924年初,李大钊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与孙中山先生会晤,两个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
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李大钊的高光时刻,他成为大会主席团的5个成员之一,参与到国民党领导的核心,颇得孙中山先生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开山之人,且做得非常出色。
那次代表大会,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质问与进攻,李大钊走上讲台,作了国共合作的专题发言,其道理气沛心清,坦荡真诚,惊为天人。他说:
“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三,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先例的一样……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他凝视着李大钊最后的照片,其藏于荷兰国家档案馆。2011年3月,唐山市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于海英女士在荷兰档案馆寻找马林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李大钊生前这最后一张遗照,拍于1927年4月被捕时,其清晰度之高,为国内所罕见。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当时荷兰驻华公使 W.J. 欧登科带回国,存入了外交部档案里,最终归入荷兰国家档案馆。
照片上,李大钊先生身穿一袭棉袍,双手下垂,大拇指贴于食指第二骨节处,呈空拳状。他双目直视镜头,可能因为睡得不好,下眼泡是肿的,但他神情淡定,目视着前方,嘴唇略张,八字胡修得很整洁。下边的胡子长出来了,脸上没有一丝的怯意,亦无喜来亦无悲,从容不迫,似乎早就预见到了归宿。
1927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倒春寒一场接一场,寒雪覆盖了北京城郭。对政治寒流,李大钊先生早就预感到了,为安全起见,他避身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按说这是很安全之地了。可是从东北闯关入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本起于草莽,一身绿林江湖习气,狡黠而机警,从不按规矩办事,他似乎最早嗅到了蒋介石的杀机,磨刀霍霍,准备清党分流,屠杀共产党员。于是,趁蒋在上海还未下最后决心时,他便先动手了。4月6日,安国军突然开车到了东交民巷,跳下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不顾苏联大使的抗议,闯进了兵营,抓走了在此避祸的李大钊。那次全城大搜捕,逮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多名共产党员。
4月7日的《晨报》登载:“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时在内者突见有许多军警趋入,闻有人向空中放手枪数响,意似报警,令人逃走……当时事出仓猝,欲逃无路,闻有藏身于烟囱者,亦有匿避于厕所者。然无一不被发见,足知搜索何等严厉矣。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唯据外人方面消息,则李大钊、路友于二人,似在其内”;“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有共产党党员名册,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册,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全名册等。又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方印一颗,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颗”;“一时许,俄国旧兵营(与中东铁路办公处毗连)有人放火,军警急驰往救援,旋消防队亦赶至,至二时始扑灭。又在该处起出重要文件甚多。放火原因,据人云,系为湮没证据之故。”
他已经不止一次来到东交民巷了。那些年,一位鲁院女同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常下榻于公安部宾馆。不时找来一拨朋友雅集,他在应邀者中,推杯换盏,笙歌夜夜。他微醺,出宾馆不远,便看到外国使馆群落。夜阑人静,总有惊魂时分。可是,他已经很难走进这段历史。是时代拒那段历史于转门前,还是那颗巨星本已经飘远?说不清楚啊,冥冥之中,他却推开首都宾馆大堂的转门。中国作协全委会和几次换届,他皆下榻于此。每次开会,他都会去东交民巷的使馆群转转,晓色、暮霭,疾步匆匆。安静的巷子里,高墙古堡,残阳夕阳明,一股历史的大风吹了过来,令他猝不及防。
李大钊被捕第三天,《晨报》又登出一条消息:“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闻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未谈党的工作,否认对北方有密谋。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也有一则消息,说:“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胡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一切行动,则谓概不知晓。”
李大钊被捕惊动了京城名流,因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皆展开营救行动。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舆论,张作霖也开始犹豫了。他麾下有好几个大军阀,他发急电给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问杀不杀李大钊。孙传芳、张宗昌最积极,而阎锡山则没有回电。张宗昌极力主张杀李大钊,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当时报刊登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赤党首要不置诸国法,何以激励将士?
随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这似乎给张作霖一个信号,他已经动手,上海血流成河,流成血海了。前有车,后有辙,蒋中正敢杀,他也不能装啊!何况老蒋给他发来密电:“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可他毕竟绿林发迹,心性多疑,总想将风险控制在最小。就是在最后一刻,各国大使给他压力,毕竟这是在东交民巷抓的人啊,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司法准则来。审就审吧,反正是走过场,所谓军事法庭,李大钊等人匆匆走了一个过场而已。1927年4月29日《晨报》记下了审判观察记: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原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布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共产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 12时10分始毕。12 时30 分即由警察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指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各党人未戴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布执行,由执行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计自 2时至 5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那个天问落成一个句号,一个生命句号,就要画下了。李大钊走了出来,朝着那个句号走去,环顾左右,身边是他的两个学生范鸿吉、张挹兰,一男一女,形同走向天国之路的护法使者。青年共产党人,国殇巨子。人生无常,死又何惜。只是他们太年轻了。范鸿吉30岁,湖北鄂城人,1918年考入北大的预科;张挹兰,35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北大教育系。他们都是最坚定的革命者,站于李大钊左右,一点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昂首相随,目光炯炯,对敌人一副蔑视之情。
东交民巷与西交民巷,世纪百年,离得有多远?若无天安门广场相隔,它原在一条纬线上,两街相连,相距不过二三里耳。初踏这个维度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入京不久,后来此地最多。离他住的军队大院也不远,可是徐步其中,西交民巷辇儿胡同中段京西看守所已经被拆了,只能从老照片上一睹明代锦衣卫狱、清代刑部监狱当年旧貌。门阙横空,两层楼高的青砖壁上,写有楷书“京师看守所”,突兀的青砖扇面上,是一幅花枝浮雕。正上方,三只狴犴,中左右各一,横卧其上,目光炯炯,欲阻凶神恶煞。正下方是一道两扇门开的铁门,米字横框加固,高墙铁窗,一锁千百年冤仇血恨。他踯躅于旧地上,仍然能捕捉到历史的气场扑面而来,他仿佛看到冷雨潇潇中,李大钊昂首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守常先生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守常态而不惊,波澜不起。他一向儒雅大度,而此刻,他声调激昂,慨然赴死,看着绞刑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一个活扣拉下了,一个黑色的句号画下了,敌人为了让他痛苦不堪,20 分钟的绞刑延长到40分钟。
一个天问落成了人生的死结,句号画下,一代巨星轰然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