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少年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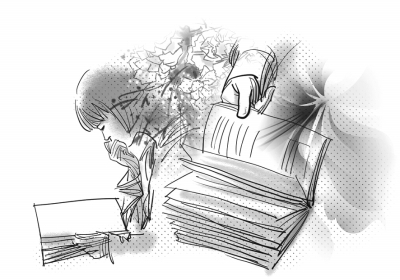 |
| 插图:郭红松 |
被雨打湿的杜甫
初三那一年的暑假,我们都是十五岁的少年。那一年的暑假,雨下得格外勤。哪儿也去不了,只好窝在家里,望着窗外发呆,看着大雨如注,顺房檐倾泻如瀑;或看着小雨淅沥,在院子的地上溅起像鱼嘴里吐出细细的水泡。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雨赶紧停下来,我就可以出去找朋友玩。当然,这个朋友,指的是她。那时候,她住在和我一条街的另一座大院里,走不了 几步就到,但是,雨阻隔了我们。冒着大雨出现在一个不是自家的大院里,找一个女孩子,总是招人耳目的。尤其是她那个大院,住的全是军人或干部的人家,和住 着贫民人家的我们大院相比,是两个阶层。在旁人看来,我和她,像是童话里说的公主与贫儿。
那时候,我真的不如她的胆子大。整个暑假,她常常跑到我们院子里找我。在我家窄小的桌前,一聊聊上半天,海阔天空,什么都聊。那时候,她喜 欢物理,她梦想当一个科学家。我爱上文学,梦想当一个作家。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物理和文学,是居里夫人,是契诃夫与冰心。显然,我的文学常会战胜她的物 理。我常会对她讲起我刚刚读过的小说,朗读我新看的诗歌,看到她睁大眼睛望着我,专心听我讲话的时候,我特别的自以为是,洋洋自得,常常会在这种时刻舒展 一下腰身。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光线变暗,父亲或母亲将灯点亮。黄昏到了,她才会离开我家。我起身送她,因为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一路逶迤要走过一条 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有人头的影子,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人,那眼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她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 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
雨下得由大变小的时候,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幻想:她撑着一把雨伞,突然走进我们大院,走过那条长长的甬道,走到我家的窗前。那种幻觉,就像刚刚读过的戴望舒的《雨巷》,她就是那个紫丁香姑娘。少年的心思,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美好。
下雨之前,她刚从我这里拿走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这场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终于停了。蜗牛和太阳一起出来,爬上我们大院的墙头。她却没 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我想,可能还要等一天吧,女孩子矜持。可是,等了两天,她还没有来。我想,可能还要再等几天吧,《晋阳秋》这本书挺厚的,她还没有看 完。可是,又等了好几天,她还是没有来。
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倒不仅仅是《晋阳秋》是我借来的,该到了还人家的时候。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她还没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雨,早停了。
我很想找她,几次走到她家大院的大门前,又止住了脚步。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比雨还要厉害地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生自己的气,也生她的气,甚至小心眼儿地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直到暑假快要结束的前一天的下午,她才出现在我的家里。那天,天又下起了雨,不大,如丝似缕,却很密,没有一点停的意思。她撑着一把伞,走 到我家的门前。那时,我正坐在我家门前的马扎上,就着外面的光亮,往笔记本上抄诗,没有想到会是她,这么多天对她的埋怨,立刻一扫而空。她不好意思地对我 说:真对不起,我把书弄湿了,你还能还给人家吗?这几天,我本想买一本新书的,可是,我到了好几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这本书。
原来是这样,她一直不好意思来找我。是下雨天,她坐在家走廊前看这本书,不小心,书掉在地上,正好落在院子里的雨水里。书真的弄得挺狼狈的,书页湿了又干,都打了卷。
我拿过书,对她说:这你得受罚!
她望着我问:怎么个罚法?
我把手中的笔记本递给她,罚她帮我抄一首诗。
她笑了,坐在马扎上,问我抄什么诗?我回身递给她一本《杜甫诗选》,对她说就抄杜甫的,随便你选。她说了句:我可没有你的字写得好看,就开 始在笔记本上抄诗。她抄的是《登高》。抄完之后,她忙着站起来,笔记本掉在门外的地上,幸亏雨不大,只打湿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句。 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看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
其实,我罚她抄诗,并不是一时的兴起。整个暑假,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我很希望她在我的笔记本上抄下一首诗。那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信,我想留下她的字迹,留下一份纪念。那时候,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的诡计多端。
读高中后,她住校,我和她开始通信,一直通到我们分别都去插队。字的留念,再不是诗的短短几行,而是如长长的流水,流过我们整个的青春岁 月。只是,如今那些信已经散失,一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倒是这个笔记本幸运存活到了现在。那首《登高》被雨打湿的痕迹清晰还在,好像五十多年的时间没有流 逝,那个暑假的雨,依然扑打在我们的身上和杜甫的诗上。
少年护城河
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我和大华曾经是死对头。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私生子,他一直跟着他小姑过,他的生母在山西,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爸,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全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
当时,学校里流行唱一首名字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我给改了词儿:“我是一 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这里黑孩子的“黑”不是黑人的“黑”,而是找不着主儿即“私生子”的意思,我故意唱给大华听,很快就传开了,全院的孩 子见到大华,都齐声唱这句词儿。现在,想想,小孩子的是非好恶就是这样的简单,又是这样的偏颇,真的是欺负人家大华。
大华比我高两年级,那时上小学五年级,长得很壮,论打架,我是打不过他的。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是因为他的小姑脾气很烈,管他很 严,如果知道他在外面和哪个孩子打架了,不问青红皂白,总是要让他先从他家的胆瓶里取出鸡毛掸子,交给她,然后撅着屁股,结结实实挨一顿揍。
我和大华唯一一次动手打架,是在一天放学之后。因为被老师留下训话,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从学校到我们大院,要经过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一块 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碑。由于胡同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经过那块石碑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蹿出一个人影,饿虎扑食一般,就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一痛拳 头如雨,打得我鼻青脸肿,鼻子流出了血。等我从地上爬起来,人影早没有了。但我知道除了大华,不会有别人。
我们两人之间的仇,因为一句歌词,也因为这一场架,算是打上了一个死结。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即使迎面走过,也像不认识一样,擦肩而过。
没有想到,第二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父亲回老家沧县给我找了个后妈。一下子,全院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原来跟着我一起冲着大华唱 “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的孩子们,开始齐刷刷地对我唱起他们新改编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哟;有个孩子,没有娘哟……”
我发现,唯一没有对我唱这个歌的,竟然是大华。这一发现,让我有些吃惊,心里有些愧疚。
我很想和他说话,不提过去的事,只是聊聊乒乓球,说说刚刚夺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就好。好几次,碰到一起了,却还是开不了口。再次擦肩而过 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嘴唇动了动,我猜得出,他也开不了这口。或许只要我们两人谁先开口,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小时候自尊的脸皮,就是那样 的薄。
一直到我上了中学,和他一所学校,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由于他比我高两年级,老师指派他教我总也学不规范的仰泳动作,我们才第一次开口说 话。这一说话,就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从当时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到毛主席畅游长江。过去那点儿事,就像沙子被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一下子成了无 话不说的好朋友。童年的心思,有时就是这样窄小如韭菜叶,有时又是这样没心没肺,把什么都抛到脑后。只是,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谁也不去碰往事,谁也不去提 私生子或后妈这令人厌烦的词眼儿。
大华上高一那年春天,他的小姑突然病故,他的生母从山西赶来,要带着他回山西。那天放学回家,刚看见他的生母,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护城河 边。他的生母,还有大院好多人都跑了过去,却只看见河边上大华的书包和一双白力士鞋,不见他的人影。大家沿河喊他的名字,一直喊到了晚上,也再没有见他的 人影。大华的生母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大家也都以为大华是投河自尽了。
我不信。我知道大华的水性很好,他要是真的想不开,也不会选择投水。夜里,我一个人又跑到护城河边,河水很平静,没有一点儿波纹。我在河边 站了很久,突然,我憋足了一口气,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冲着河水大喊了一声:大华!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喊了第二声:大华!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心里悄悄 想,事不过三,我再喊一声,大华,你可一定得出来呀!我第三声大华落了地,依然没有回应,一下子透心凉,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哇哇地哭了。
就在这时候,河水有了哗哗的响声,一个人影已经游到了河中心,笔直地向我游来。我一眼看出来,是大华!
我知道,我们的友情,从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彼此谁有点儿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就像真的有什么心理感应一样,保证对 方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我们两人都相信,这不是什么神奇,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就是友情。罗曼·罗兰曾经讲过,人的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 但真正的朋友,一个就足够。
油条佬的棉袄
在我们大院里,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俩儿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 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婶们常常拿他们哥俩儿开玩笑,说你们不是你妈亲生的吧?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
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他们在我们老街的十字街口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在那里炸油条。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 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 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着牛大爷和牛大妈的炸油条赚的钱长大的。
大牛上高一的时候,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长过了小牛一头多高,而且比小牛长得更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抹头 发,让小分头光亮些。那时候,他特别讨厌我们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自己的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 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的通知单,他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老师问,就说是爹妈病了。
小牛和哥哥不大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的面前,总有点儿抬 不起头。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拿起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有意 无意是明显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大牛高三那年,小牛初三。两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了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在十字街口炸油条,用沾满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
小牛中专四年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五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 没两年,大牛就结婚了。结婚前,他回家来了一趟,跟爹妈要钱。具体要了多少钱,街坊们不知道,但街坊们看到大牛走后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很生气,平常常见的笑 脸没有了。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
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了下坡路。没几年的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 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了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了长假回家伺候。老两口的吃喝拉撒睡,外带上医院,都是小牛一个人忙乎。大牛倒 是回家来看看,但看的主要目的是跟爹妈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 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唯一的一次,牛家老两口没有给大牛钱。大牛臊不搭搭地走了,就再也没进这个家门。
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有五六年的样子,先后脚地走了。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有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支支吾吾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舍不得扔。他拿起棉袄,忽然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响。他用手摸 摸,棉袄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我爸爸行政20级,每月只拿 70元的工资。这时候,小牛才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的含义。
这之后,小牛就离开我们的大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哥俩儿。
五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作《蛋佬的棉袄》。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 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但母亲去世后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有一根金条。“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 脱掉。”唱得一往情深,让我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的破油棉袄。
肖复兴 1947年生,原籍河北沧州,现居北京,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文学作品50余部,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
